第一章 红糖与骗局1978年的秋老虎格外凶,晒得柏油路面软乎乎的,踩上去能粘掉鞋底子。
赵春兰坐在颠簸的拖拉机后斗里,手心攥出的汗把蓝布褂子的袖口洇出深色的印子。
她斜挎着的帆布包里,装着娘连夜烙的十张玉米饼,还有一双纳了半年的布鞋——媒人说,男方是镇上的手艺人,叫张老实,人如其名,踏实肯干,就是家里穷点,没穿过像样的鞋。
“春兰啊,到了地方可得懂规矩,”媒人是个胖婶子,脸上的肉随着拖拉机的晃动一颤一颤,“张师傅虽说比你大几岁,但他没结过婚,你嫁过去就是正头娘子,不比在山里刨地强?”
赵春兰点点头,心里像揣了只兔子。
她十九岁,在村里算老姑娘了,娘急得嘴上长燎泡,好不容易等来这门亲事。
镇上、手艺人、没结过婚,这三个词在她心里盘了无数遍,每一遍都长出点甜滋滋的盼头。
拖拉机在一个挂着“红星镇”木牌的路口停下,胖婶子拽着她往一条窄巷里钻。
巷子两旁是挤挤挨挨的土坯房,墙头上爬着拉拉秧,空气里飘着煤烟味和说不清的腥气。
走到巷子尽头,一扇掉漆的木门虚掩着,胖婶子推开门喊:“老张,人给你带来了!”
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从屋里迎出来,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,袖口磨出了毛边,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蚊子。
他看见赵春兰,咧开嘴笑,露出两颗泛黄的门牙:“来了?
快进屋,屋里凉快。”
赵春兰跟着他往里走,院子里堆着些木头和铁皮,像是做手艺的地方。
正屋门帘一挑,突然窜出两个小孩,一男一女,怯生生地看着她。
男孩约莫七八岁,光着脚丫,裤腿卷到膝盖;女孩更小点,梳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,睁着黑葡萄似的眼睛,眼神里却藏着警惕。
“这是……”赵春兰的心猛地往下沉。
“哦,这是建军和金凤,我……我侄子侄女,暂时放我这儿养着。”
张老实挠挠头,眼神有点躲闪。
赵春兰没说话,脚像钉在地上。
她不是傻子,这两个孩子看张老实的眼神,分明是亲爹。
胖婶子在旁边打圆场:“瞧这孩子,还害羞了。
老张是个好人,前妻走得早,带着俩娃不容易,你来了正好帮衬着,将来生了自己的娃,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……”前妻?
娃?
赵春兰的耳朵嗡嗡作响,像被谁用闷棍打了一下。
她猛地回头看胖婶子,对方眼神闪烁,不敢跟她对视。
骗局。
从头到尾都是骗局。
她不是来当正头娘子的,是来给人当填房,当后妈!
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,她转身就想往外跑,胳膊却被张老实死死抓住。
“春兰,你听我解释,我不是故意骗你,我就是……就是怕你不来。”
他的声音带着哀求,“我知道委屈你了,但我保证,以后一定对你好,有我一口吃的,就有你一口。”
赵春兰挣扎着,玉米饼从帆布包里掉出来,滚了一地。
她看着那两个孩子,男孩把女孩护在身后,眼神像小狼崽子似的,充满了敌意。
她又想起山里的娘,想起那句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”,腿一软,瘫坐在地上。
哭有什么用?
跑回山里,娘能容她吗?
就算容了,往后谁还会给她说亲?
那天晚上,赵春兰躺在张老实身边,浑身僵硬得像块石头。
土炕硌得骨头疼,旁边男人的呼吸声粗重得像拉风箱。
她睁着眼睛看着黑黢黢的房梁,眼泪无声地往枕头上淌。
半夜,张老实翻了个身,塞给她一块东西。
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,赵春兰看清是块红糖,用油纸包着,方方正正的。
“吃块糖,”他的声音在黑暗里闷闷的,“甜丝丝的,日子就好过点了。”
赵春兰捏着那块红糖,糖纸粗糙的纹理蹭着掌心。
她没吃,把糖塞进了枕套里。
在这个陌生的屋檐下,这是她收到的第一样东西,也是她和这个男人之间,唯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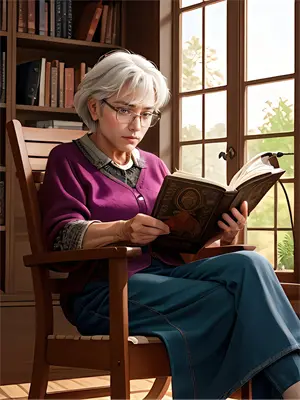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